摘自:《独家人物》2020年第1期
作者:王芹
二、
我的母亲有个伯父住在青岛,当时已年近七旬,没有子女,夫人也去世了,于是便邀侄女们来青岛同住,以便互相照应。我们这位伯外祖是北京旗人,原本姓李,年轻时因反对包办婚姻,愤然离家出走,投奔他在广东任职的舅父,因而改姓伊。1912年他去了青岛,创办过《青岛白话报》等,也算是个老报人。这位老人自己有房子,有些积蓄,据说是个思想活跃,谈吐风趣,文采风流的人。
起初父亲对此事还有些犹豫,觉得不到万不得已,谁也不愿意寄人篱下,况且毕竟北京是自己的家,老母亲还健在。可是,此时他们的生活已很窘迫,伯外祖已将路费寄来,诚意感人。于是他们便带着我母亲的妹妹一同去了青岛。有意思的是,这位老伯父还让他们从北京给他买副弓箭,于是他们只好去旧货市场里寻找,后来还真淘着给他带去了。
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,青岛的气候很适合他养病。他后来在回顾1937年的境况时说,自己决定“在此住一夏天,陪着阔人们避暑,休养我的身体,恢复我的健康,为预备我的衣食,继续效力。但是我还需要回去,结果我身边的一些文字债务,我觉得这样才能维持我的‘文丐’资格和信用。” (见《海滨忆写》,1938年6月2日《青岛新民报》)
而后来的事情则是始料不及的:1938年初日军侵占青岛,为避战事,城里的许多人都撤离了,有的去上海租界避难,有的去了后方,农村有亲属的也挑着行李回老家了。不久,伯外祖的房子就被日军霸占了,家产损失殆尽,连桌椅都被日军当柴烧了。这一家人无处可去,只好随着老人东躲西藏。
宁波路的一片老房子当年都是青岛巨富刘子山的,青岛沦陷后,许多房客都撤离了,这里便空出来了许多房子。伯外祖听说这里有空房,便令人撬开门,率全家搬了进去。他说:没事儿,他同管房子的认识。从此一家人便在这里租房住了下来,父亲随即给自己起了个新的笔名“度庐”,他说“度”就是“渡”,希望能够“混一混”,度过这一段艰辛的日子,期待渡向彼岸。

宁波路4号院里的这栋小楼,就是父亲居住过十多年的地方。他在青岛创作的数十部小说,包括其代表作“鹤—铁五部曲”(即《鹤惊昆仑》《宝剑金钗》《剑气珠光》《卧虎藏龙》《铁骑银瓶》),都是在这里写成的。这是一栋二层小楼,北面还有地下室。原来的院门是朝西开的,对着现在的上海支路,沿着几磴石阶上去,有两扇木门。现在这个院门已经被封死了,院中的人改由北面后盖的一栋板楼的门洞里进出,门洞的旁边挂着一块“王度庐故居”的牌子,因为要去故居必须经过这里。
这里地势较高,在一片杂乱的各式建筑之中,还能看出那一幢幢历经风雨,样式大同小异的红顶德式小楼。这张照片是2007年从故居的西面拍摄的(图5),可以看到院墙上还留有原来院门的门柱。由照片中小楼左边的那个小门进去,是一层的楼道和通往二层和地下室的楼梯。我家住在一层的西边,那个小门右侧的两扇窗内就是我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。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,左边的一扇小窗原来是个门,而父亲的书桌就摆放在右边的那扇窗下(现被树挡着)。这栋楼里当时还住着几户人家,楼上一家的男主人在海关工作,生活条件较好。我出生那年生活艰难,他家常送一碗粥来给我喝。
关于上述变故,父亲在《海滨忆写》一文中仅作了一点概述:
去年樱花开的时节,我由北京初次来到青岛,目的第一是看望多年未晤的戚友,其次便是因为我过了多年的写作生活,把身体弄坏,需要觅一个适当的地方休养几个月。……然而,命运,不久便发生时局的变化。
把避暑变成了避难,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,度了半载多的恐怖生活……自然,在我是侥幸的,然而我的身体却因为一往的忧患,需要更长时期的休养了,换句话说:我需要更长时期地住在青岛了……
“时局的变化”,当然是指“七七”事变和青岛沦陷,同时也透露了父亲此时的处境:日寇统治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已经快半年了。父亲来青岛时,本想能在这里觅得一份较稳定的工作,可是这时已身不由己了。他虽然只是个文弱书生,可是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、不卑不亢,可以想象得出,他的内心有多么痛苦。但是为了养活家人,为了能在沦陷区不失尊严地生活下去,他只能卖文为生。
《河岳游侠传》是父亲第一次使用“王度庐”这个笔名写的武侠小说,于1938年6月1日开始在《青岛新民报》上连载。11月15日连载结束,16日又开始连载武侠悲情小说《宝剑金钗记》,署名也是王度庐。
1939年4月24日,《宝剑金钗记》尚未连载完,该报又开始连载父亲写的另一部社会言情小说《落絮飘香》,署名霄羽。也就是说,此时同时有两部不同类型的小说在该报连载,而作者都是我父亲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,接着连载的武侠悲情小说为《剑气珠光录》《舞鹤鸣鸾记》《卧虎藏龙传》《铁骑银瓶传》《紫电青霜录》等,署名均为王度庐;而“并行”连载的社会言情小说为《古城新月》《海上虹霞》《虞美人》《寒梅曲》等,署名则为霄羽。
其间,1940年8月16日南京的《京报》也开始连载父亲的小说,第一部是侠情小说《风雨双龙剑》,之后又接连刊载了《彩凤银蛇传》《纤纤剑》《舞剑飞花录》《大漠双鸳谱》《春明小侠》《琼楼双剑记》(后两部因存报缺失,文本不全),署名亦均为王度庐。这种同时在两份报上有三部小说连载的状况,也持续了几年。从1938年至1945年,父亲共创作了十余部侠义、侠情小说,数部社会言情小说。据我母亲说:他写东西很快,并不十分推敲字句,不留底稿,也无资料可查。父亲身体不好,除伏案写作外,即卧床休息,他不应酬,不管家务,不在乎环境嘈杂、孩子吵闹,对物质生活也无要求。在这样艰难困苦、心情压抑的状况下,他的创作却达到了成熟期。
1945年后,父亲还用过鲁云、绿芜等笔名。由于他的作品多为连载小说,又逢时局动荡,常常一篇小说尚未登完,报馆却关门了,因此还会有一些尚未发现的笔名和作品。目前见到的从1946年至1949年初的作品有:在《军民晚报》上连载的侠义、侠情小说《龙虎铁连环》《金刚玉宝剑》《玉佩金刀记》,署名王度庐;在《青岛时报》上连载的侠义、侠情小说《紫凤镖》《宝刀飞》《雍正与年羹尧》(即《新血滴子》)、《清末侠客传》(即《绣带银镖》)、《太平天国情侠图》,署名鲁云;在《青岛时报》上连载的社会言情小说《晚香玉》《粉墨婵娟》侠情小说《燕市侠伶》,署名绿芜。还有连载于青岛期刊《民民民》上的《锦绣豪雄传》,连载于上海《戏世界》的《铁剑红绡记》等,亦均署名王度庐,但因残存文本稀少,难以考辨是否包含伪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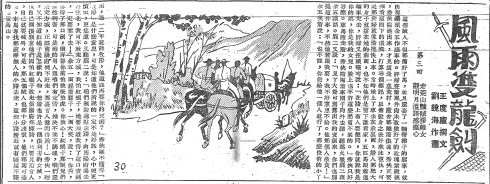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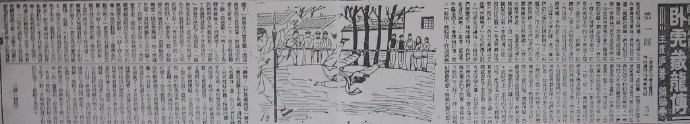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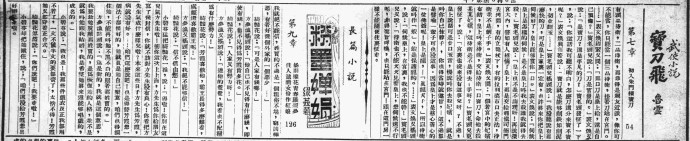
父亲1938年后的著作主要是侠情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,侠情小说多以清代为背景,社会小说则多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战前,而地点多被设置在北京。北京是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,他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、民风民俗,而且那里还有他的母亲。他只能在小说中寄托自己的乡愁,通过小说里的豪杰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故事,一吐心中之块垒。想起父亲在北京时写的那些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杂文,更能理解他此时内心的苦闷。以前他还写一些诗词、杂文,但这一时期除《海滨忆写》这样偶尔为之的杂文之外,他却只写小说了,其原因可想而知,尽管不得已生活在沦陷区中,仍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,坚守自己的民族气节。
父亲的许多小说后来都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加以出版(少数由其他出版社印行),该出版社的经理刘汇臣为宁波人,办事精明果断,出版我父亲的书,他是经过深思熟虑,周密策划的,有些书名的改动或另行命名应该都有他的主意,其间渗透着精明的市场意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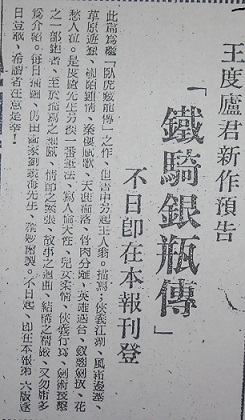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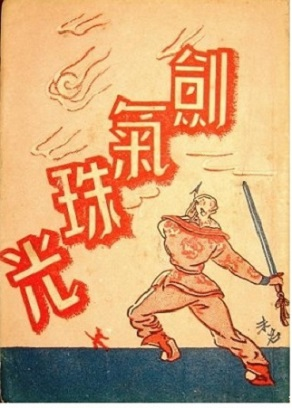
由此想起一件有趣的事:侠情小说《舞剑飞花录》连载于1943年1月23日至1944年1月18日的南京《京报》,共18章,约25万字;1949年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出版,改题《洛阳豪客》。后来我们在整理资料时发现,虽然《洛阳豪客》源自《舞剑飞花录》,却与《舞剑飞花录》有许多不同之处,此书共16章,约14万字,不仅回目与连载时不同,文字也有一半不同。也就是说,在《洛阳豪客》全书约14万字中,有一半文字是断断续续地从连载小说《舞剑飞花录》中复制过来的,而另一半文字则是重写的,包括开头和结尾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以我猜想,可能是当年刘汇臣去索稿时(1948年前后),父亲既无《舞剑飞花录》的手稿(1943年已交南京报社),亦无全部连载报纸(因为远居青岛),于是就利用手头尚存的连载报纸,加以相当程度地重新创作,从而成为一部另有新意的可观文本,并得到刘汇臣的认可和赞许。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不止这一部。(未完待续)
